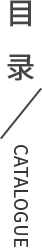《一纸婚约》爱情友情的双重背叛,谁是雨后的那一抹阳光?
电影在尾部的时候,总是会出现王老师心灵鸡汤一般的话。虽然这部电影的主角并没有什么名气,但是张辉还是和刘熙阳用自己最专业的一面去对待整个电影,而摄影方面虽然不能说百分百的完美,但是至少可以说处理的非常好。抨击着观众的心灵。不多不少刚刚好让观众心里有了震撼。无论我们遇到了谁,他都是我们生命应该遇到的人。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,那都是我们人生应该经历的事情。那就是正确的。禁止抄袭!欢迎评论,
《前任3》:能够握紧就别轻易放手
就像电影里,林佳陪着孟云度过了最开始的创业艰苦期,一起吃泡面是最真实的细节,省吃俭用只舍得看周二的半价电影是最甜蜜的生活,创业时聚少离多,会疏于关心对方也是真的,两个人一同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却无法共富贵,是电影中留给我们的遗憾,也是生活里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现实。你也许会希望每个人的生活中,都不要像电影里那样,明明相爱,却错过了。也会不自觉的想像着,如果能回到过去,如果没有遇到他或她,如果没有彼此一起经历的那段时间,如果是另外一个人,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。可是即便再给你一次机会,哪怕遇见一个非常完美的人,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爱,依然不会有好的结局。所以啊,你遇见的,其实就是最好的。如果有些人在感情中少了挫折和遗憾,那一定是因为,在爱的时候,留住了爱。在可以珍惜的时候,学会了珍惜。
高跟鞋,白丝裙,粉外套,朴赞郁的暗喻,美得令人窒息!
包括昆虫、钢琴、冰淇淋、红酒、叔叔做的牛排、信件……这些细节都不仅在充盈着画面,还牵引了剧情的发展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,斯托克帮母亲梳理着一头浓密的红色直发,画面逐渐过渡到野草、到一片广阔的绿色、镜头在拉近,斯托克和父亲在草丛中狩猎的回忆缓缓展开。从茂密的梳头画面过渡到暗流涌动的狩猎画面,在的镜头中,画面不再是为了美观,而成为了一种引领倒叙结构的工具和领导。
说《前任3》侮辱中国电影的,是“精英优越感”在作怪
亏着别人的钱,然后把电影当成精英的标签,构建起对商业片的鄙视链,这不显而易见嘛,看的人少,排的自然就少喽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,可不可以通过多建影院,增加银幕总块数的方式,
二代妖精:为人妖婚姻合法化疯狂打call!
团购包场团体票、团体合作电影包场、浪漫求婚商家联盟资源互换联盟合作联系人张经理:刘经理:董经理:星美国际影商城期待与您的合作爱生活爱星美
他设计的电影海报,呈现的不仅是东方美学
很多时候,电影内容在人们心中都已经渐渐淡化了,但黄海设计的海报画面却依然清晰,而且能让人在看到的瞬间就回忆起电影的内容。黄海说,要的就是这个效果!
《前任3》:那些不好好分手的人其实谁也不爱,连自己也不爱
“分手”这件事,无论谁先提出,都代表着“失败”、“结束”、“戛然而止”的意味,其实是ta不能坦然面对那个“失败的”、“半途而废的”、“前功尽弃的”自己,犹如一个搭着积木的孩子,当积木突然倒塌,ta不能接受是自己玩坏了,于是要么赶紧逃开,要么就把责任完全地推给别人,甚至会哇哇大哭着表达着伤心,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,只有这样,自己才能给自己交代——所以,那些不会好好说分手的人,其实是不接受自己自己的无能、也不爱自己。分手见人品,其实分手更见人格,他是否爱过你,他是否值得爱,你和他当初是否拥有过成熟的健康的关系,我们都会从分手的过程里看得通通透透。
Day 343 “当电影不再是电影时”
当一次采访中,法斯宾德回答说:“他们有可能,但着对本片并无害处,反倒有益于他们自身的现实——我认为这是根本之道。影片必须在某一时刻不成为影片,而是开始活起来,使你问道:我和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光景?……”甚至它也可以和我们目前熟悉的、发生在欧洲的“移民新闻”完全脱离,和《玛利亚·布劳恩的婚姻》灵动的摄影不同,《恐惧吞噬灵魂》的世界是静态的,法斯宾德将人物反复放置在门、窗、楼梯栏杆构成的画框内,让人物反复说着简单的对话。ChrisFujiwara说整部影片弥漫着一种“永恒之感”。非常难以置信,法斯宾德就这样让纯粹到极致的爱,让我这样的观众感到信服。究其原因,他拍出来的亲密和孤独是可信的,也是美的,更重要的是他所说的“当电影不再是电影时”,要能让电影成为观众自己的人生。
“好色者”张艺谋的头号难题:电影的商业与艺术如何兼顾?
黑色展现了秦国的威严和历史的残酷,象征着铁器时代的风貌;红色则映照着爱欲,占有,伴随着剑雨腥风,象征着历史兴衰灭亡的血液;绿色形式上是模仿山川,光可以看做白色,水也可以看做白色,风也可以看做白色,它是最真实,本质,纯粹的象征。《英雄》这种极度写意化,舞台化的表现,成就了电影视觉世界的空前美景,其色彩的运用媲美黑泽明的电影经典《乱》。
《北方一片苍茫》与不断走向“现实”的中国艺术电影实践
总之,我们可能正身处在中国当代电影的一场大变革的前夜。除了为终于到来的这一幕感到欢欣鼓舞之外,我们的理论和批评话语也需要尽快与之相适应。在业界已经不断做出表率的今天,对于中国当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挑战,恐怕早已太过不言而喻。